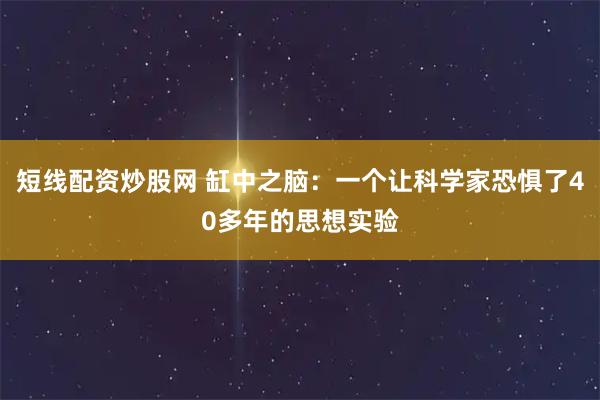
 短线配资炒股网
短线配资炒股网
作者 | Talk君
大家好,我是talk君。
在澳大利亚的一间实验室,科学家们将80万个实验室培养的人类脑细胞放置在装有微电极阵列的培养皿中,这些神经元通过电流刺激学习玩一款简单的乒乓球游戏。
令人惊讶的是,这些细胞仅在5分钟内就掌握了游戏规则,其学习速度远超任何人工智能系统。
这项实验的领导者布雷特·卡根博士可能没有想到,他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与一个古老的哲学噩梦如此相似——那就是“缸中之脑”思想实验。
哲学噩梦:40多年的思想实验
1981年,美国哲学家希拉里·普特南在《理性,真理与历史》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“缸中之脑”假设。
他设想一个邪恶科学家将人的大脑从身体取出,放入装有营养液的缸中,通过计算机连接其神经末梢,模拟外部世界的电信号。

大脑接收到与原来完全一致的电信号,就会认为自己仍然正常生活着,无法意识到自己已沦为缸中的实验对象。
普特南提出这个思想实验不是为了恐吓我们,而是为了挑战传统的 “形而上学实在论”。他想证明,我们无法脱离自身的概念框架去谈论独立于心灵的客观现实。
古老先声:跨越千年的相似思考
尽管“缸中之脑”是现代概念,但类似思考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。
两千多年前,中国哲学家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,醒来后不禁思考:是庄周梦中变成了蝴蝶,还是蝴蝶梦中变成了庄周?
这个“庄周梦蝶”的故事与缸中之脑有着惊人的神似。

17世纪,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假设可能存在一个“邪恶魔鬼”,为他虚幻出包括天空、空气、土地、色彩、声音在内的一切感知,让他误以为自己活在现实世界中。
笛卡尔甚至怀疑自己可能“既没有双手,也没有双眼,也没有肉体,也没有血液,也没有一切的器官”。
科学现实:缸中之脑正在走来
随着科技发展,“缸中之脑”已不再是纯哲学假想。
2025年,澳大利亚初创公司Cortical Labs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生物计算机CL1。这款设备使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神经元集群,这些神经元生长在硅芯片上,能够通过电极与系统交流。

CL1的体积不比鞋盒大多少,内部有数十万个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神经元,数量介于蚂蚁与蟑螂的大脑之间。
这些神经元不是从大脑中直接取出,而是用诱导多能干细胞(iPSC)培育而成。
研究人员通过电极向神经元发送电信号:当神经元回答正确时就给予鼓励信号,错误时就收到惩罚信号。
这种奖惩机制使得这些神经元能够快速学习,甚至学会了玩《乒乓》游戏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,在一些实验中,人类和小鼠的神经元竟然学会了一起玩电子游戏。而在另一个实验中,培养的人脑细胞团上甚至发育出了一对简单的眼睛结构。
认知困境:我们如何确定真实性?
“缸中之脑”实验揭示了人类认知的脆弱性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完全依赖于神经信号的解读。
我们看到花朵的艳丽,是因为光线反射进入眼睛,转化为神经信号;我们听到鸟儿的鸣叫,是因为声波引起耳膜振动,进而转化为神经信号。
但在“缸中之脑”的情境下,这些信号的来源被篡改,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非来自真实世界,而是计算机的模拟。
由于大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这些神经信号,它完全无法确定这些信号是来自真实世界还是虚拟程序。
笛卡尔曾提出“我思故我在”,强调思考的主体存在的确定性。
然而,“缸中之脑”假设让我们意识到,即便我们能够确定自己在思考,但思考的内容是否与真实世界相符,却始终是个谜题。
虚拟宇宙:可能性的拓展
一些思想家将“缸中之脑”的逻辑扩展到整个宇宙。
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·查尔莫斯提出“模拟假设”,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物理世界可能本身就是更高维度的数字模拟。
类似电影《黑客帝国》中描绘的,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机器创造的虚拟世界里。

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·博斯特罗姆通过数学论证提出,若文明发展到能模拟宇宙的技术水平,多重嵌套的虚拟世界将呈指数级增长,我们身处真实宇宙的概率反而微乎其微。
无法证明:困境与出路
残酷的事实是: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。
现代神经科学表明,大脑的前扣带回皮层与躯体感觉皮层协同工作,能在没有实际物理刺激的情况下,仅凭想象就产生真实的疼痛感知。
在一项2017年的实验中,受试者在虚拟现实中经历“断手”场景时,其大脑的痛觉中枢活跃度与真实受伤者别无二致。
量子力学中的“观测者效应”与“双缝干涉实验”暗示,物质世界的形态或许依赖于观测者的意识——这与“缸中之脑”中外部世界由信号构建的假说不谋而合。
即使我们真的只是缸中之脑,或许也不必绝望。真正的出路可能在于:珍惜当下体验,无论它来自真实还是模拟。

也许有一天,我们能够回答这个困扰了人类两千多年的问题。但无论如何,对真相的追寻本身,就是人类存在的最美证明。
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~
赶紧关注视频号@一刻talks吧!
亿通速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